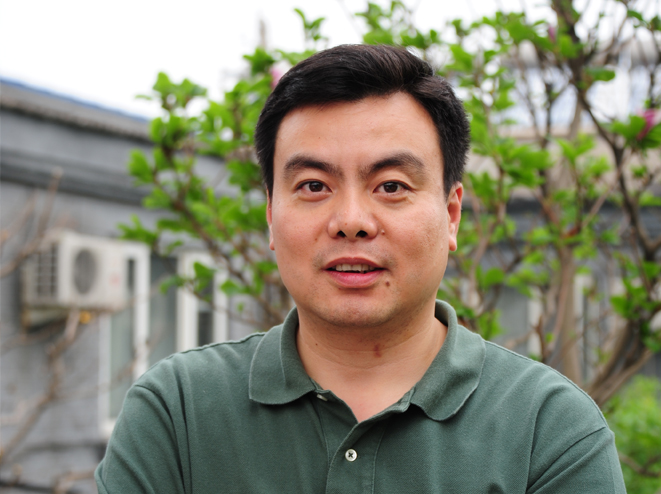【導語】數字背后的雙重撕裂?
?
1. 專業設置的時間黑洞?
教育部雖在2020年增設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專業,但《新工科建設成效評估報告2023》指出:31.5%的新設專業因師資設備不達標淪為“紙上專業”。更諷刺的是,某“雙一流”高校機器人工程專業,竟由機械學院教師集體轉型授課,教授們坦言“現學現賣”。
?1. 制造業的“高薪孤島”?
河南省2023年鄉村振興專項招聘中,985院校畢業生報名占比僅7.3%(省人社廳數據)。這種“寧送外賣不下鄉”的集體選擇,折射出?“身份經濟學”的剛性約束?:一線城市送外賣月均收入6000元,且享有“都市白領”身份想象;而基層崗位即便提供編制,也難以抵消“社會地位降級”的心理成本。
?1. 就業補貼的逆向激勵?
盡管教育部力推“現代產業學院”,但某汽車零部件企業與高校共建的實訓基地,因校方要求“不得影響正常教學秩序”,每年僅開放45天。企業總工程師苦笑:“這就像讓游泳隊在浴缸里訓練奧運會。”
?1. 建立“產業-教育”旋轉門?
將基層服務經歷與城市落戶、職稱評定剛性掛鉤。浙江省2023年規定,?鄉村振興服務滿3年可獲大城市落戶加分?,某縣農業局當年985院校報名率提升18個百分點。
華為“天才少年”計劃已證明能力定價的可能性。需建立?國家級技能認證平臺?,允許工程師資格、數字技能等“能力貨幣”跨行業流通,打破唯學歷論的封閉體系。
蔡義鴻先生十五年前警示的“就業難悖論”,在數字經濟時代展現出更復雜的形態。當“慢就業”成為青年常態,當產教脫節演化為制度性梗阻,我們更需要您當年的銳氣,刺破“教育產業化”的精致偽裝。歷史終將證明,解決人才困局的關鍵,不在于培養更多大學生,而在于?重建知識生產與價值分配的制度正義?。
中國正在進行著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可以說在這一進程中,各行各業需要大批的人才,但近年來擺在我們大學生面前的卻是就業難這一殘酷現實,可以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悖論。
看看這幾個月發生的畢業生求職悲喜劇。石家莊女大學生投水自殺,身后留下10萬字的求職日記;北方工業大學15名應屆畢業生集體上網“拍賣”,叫價月薪2000至3000元;還有濟南女生街頭發求職啟事,應聘“專職太太”、“2009大學生就業”大戲剛拉開大幕,就被渲染得如此悲壯。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9年《經濟藍皮書》中稱,截至2008年底,有100萬名大學生未能就業。而2009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2009年大學生就業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學生就業最艱難的時期。
今年兩會期間,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預測,今年大概只有300萬的學生能夠找到工作。
有人把大學生就業難歸結于經濟危機。今年3月,上海對外發布的調查報告稱,受金融危機影響,當地逾半數外企今年不招收應屆生,其他有招聘計劃的企業崗位數量也極有限。如果將就業問題歸之于金融危機,那為何去年還有100多萬大學生未就業?
也有人將就業難怪罪于高校擴招。據統計,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559萬人,比2007年增加64萬人;而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進一步增大到611萬人。但問題是,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會抱怨自己的大學生太多?
更有網友呼吁:恢復分配制度!但所有人都明白,市場經濟越來越發達,畢業生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市場化。這種雙向的自由選擇的就業模式,畢竟是一種進步。
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表示,大學生就業難將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趨勢。但他認為,大學生數量不是就業困難的主要因素,因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勞動力是來自大學畢業生,“質量問題才是關鍵”。
筆者深表認同,我國的大學生質量問題,主要跟我國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模式有關,我們的大學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現象——我們的天之驕子中,有許多連小麥苗與韭菜苗都區分不了,有許多不知道什么是五谷雜糧,有許多不會修理桌椅、換個燈泡燈管等日常生活小事,有的甚至連生活自理能力都有問題。
當然,還有就是跟大學生好高騖遠的就業心態有關,公務員、大企業、大城市固然值得向往,但中國眾多的中小城市、鄉鎮企業和農村基層,同樣是大學生驕子們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
中國的大學生數量并不多,尤其是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我國廣大農村正亟需大量優秀人才,但我們需要的不是嬌生慣養、五谷不分、高分低能的大學生,我們需要的是吃苦耐勞、勇于創業、德才兼備、放眼未來,敢于將自己融入到中國快速推進的城市化浪潮中的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