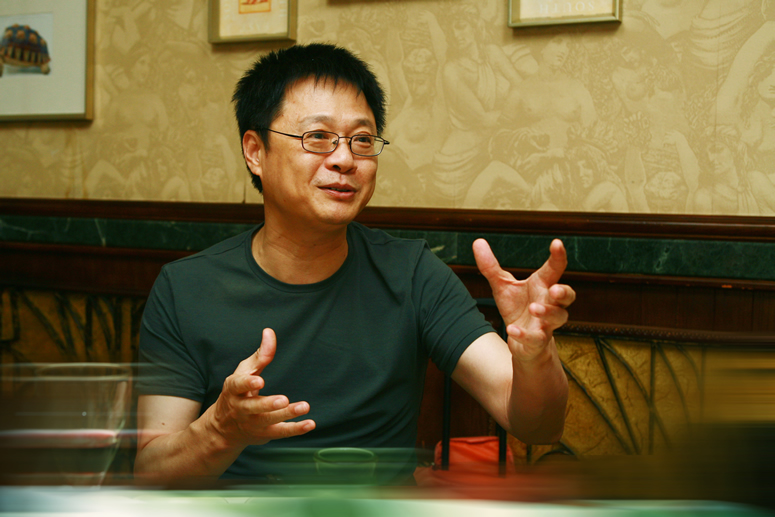守望傳統于我輩而言,似乎漸行漸遠。記得大概是1970 年,筆者剛剛五歲,身體還很硬朗的奶奶就逼我爸和幾個姑姑、小叔給她出錢出力,打了一副上好的松木棺材,平時就擺在廳堂一側,里面可儲存谷子或玉米,蓋上蓋子可以當長條板凳用。白天,我和堂弟堂妹在外面玩累了回家經常趴在上面睡覺,從沒有任何異樣的感覺。而奶奶從此跟人聊天,極喜提及自己已經備好的棺材,一直很是自豪的神態。村里村外其他還沒有備好棺材的同齡老人,也因此愈發緊迫催促自己家人想法置辦。在我們當地老人的眼里,那副棺木就是她來生的房屋和住所,在貧困的現世有了屬于自己的一副棺木,就保證他們的靈魂將不會在另一個世界里流離失所。而孩子們的孝悌也說明了他們的能耐,確保了本族一脈的老人提前解決來世的歸宿,實在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一直到十幾年后我大學畢業,奶奶仙逝,那副棺材才真正派上用場。在桂西壯族鄉村,任何冒犯老人和祖先的語言、行為都會被視為最大忤逆,遭受父老鄉親的強烈譴責,無處藏身。早早就為老人置辦棺木也成為每個年富力強的戶主必須的責任,即使那時候極其貧困,文革所謂斗私批修鬧得人人自危,也不敢指摘這樣的習俗,更不可能大張旗鼓地觸犯老人的棺木。然而這兩年來在一些地方出現的鬧劇,其荒唐至極遠遠超出了想象。看到這樣的新聞,令我不寒而栗,心底里不禁為奶奶感到某種慶幸。
遠者如兩年前在河南省周口、洛陽等市掀起的“平墳復耕運動”,導致輿論大嘩;近者如日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安慶毀棺事件,余波未平。據5 月29 日新華網圖片新聞顯示,5 月24 日,桐城市新店村一次就銷毀了40 多副成色一新的棺材,全部拋棄在村邊的荒地上。5 月25 日,該市一位宣傳部副部長表示,桐城全市總共有4.6 萬副棺木,已經處置(銷毀)的約4.5 萬副,剩余800 左右棺木仍保留在居民家中。為地方官員口氣中的自得和滿足背書的,卻是十幾位老人提前以不同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用“自盡”來保全自己全身入土的夙愿。簡單粗暴的措施背后,其實都是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財政的需要。各種前所未有、令人瞠目的“苛政”、“杰作”不過是權勢與資本合謀開出的惡之花。由此來觀照城鎮化中歷史文化傳承與保護,愈發覺得前景的黯淡與無望。
以擁有數千年文明歷史而自傲的中國,理應也塑造出對厚重歷史膜拜、敬畏的傳統。倘若如此,即使在轟轟烈烈的城鎮化大浪潮之下,古城和文物的保護不會成為話題。但不幸的是,“不破不立”同樣在我們主流意識里占據重要地位,在事關生存與發展的大訴求之下,古城和文物的保護便一直就是個話題。
由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一事的演變走勢,不難見出歷史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在城市的發展中,面對權勢與資本合謀是何等的無奈。據兩年前新華社報道,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3 號四合院( 現為24 號院) 在1931 年至1937 年期間曾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租住。這一時期是兩人對中國建筑史及文物保護做出重要貢獻的時期。2009 年,因涉及商業項目,24 號院門樓及西廂房被先后拆除。2012 年事件被媒體曝光之后,曾一度掀起軒然大波,當事的開發企業辯稱是“維修性拆除”;相關專家則一致認為,梁林故居被拆這一出鬧劇,開發商應該負刑事責任!政府相關主管部門也應受到處罰!然而時至今日,此事已然悄無聲息,似乎不了了之。保護人士的奔走與吶喊,在輿論的集體麻木如死水面前似乎都翻不起任何漣漪。
對此,有人還對所謂的文物法規,或者更高一級管理部門的作為心存僥幸。其實在涉及土地、在涉及GDP 的大訴求之下,沒有最荒唐,只要更荒唐;而每個荒唐的背后都隱藏著權勢與資本的魔影,或者單獨粉墨登場,或者一前一后演雙簧,或者合謀操縱……
而城鎮化的浪潮,人口的急劇流動,加速割斷了人們與地緣的聯系,此人奉若珍寶的祖物于彼人而言也許不過是敝帚自珍,連自己故土、家園都變得越來越遙遠、朦朧的時候,何來對他鄉的依戀,對他鄉傳統的敬畏!當權勢與資本合謀為攫取不可告人的利益時,如果說沒有默默地利用這種土壤和氛圍,誰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