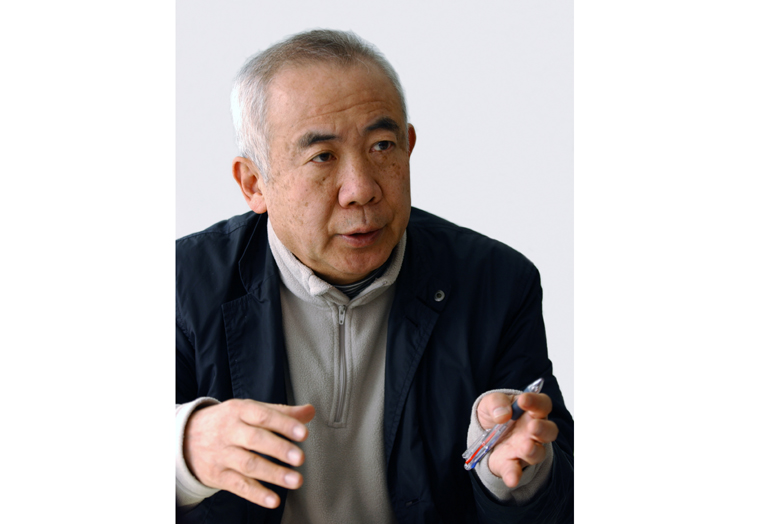芒福德建筑評論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標(biāo)準(zhǔn)在于,他非常強調(diào)建筑所賴以建立的全部人文背景和環(huán)境。他認(rèn)為,建筑不過是更大的人文環(huán)境或者自然景觀中一個小小的元素。因而,有靈感的建筑物,就要求有靈感的城市規(guī)劃。
芒福德對于人類未來的城市形式和質(zhì)量十分關(guān)心、十分熱忱,正是這種興趣激勵了他去研究人類以往的城市。他曾指出,要建設(shè)新城鎮(zhèn),首先就要為城市找到一個全新的形象;而若不清楚理解歷史上健全城市具備哪些特點,若不清楚歷史上人類在城市規(guī)劃中所犯過的錯誤,也就無法設(shè)想出這樣一個全新的城市形象。
城市——如人們從歷史上所觀察到的那樣——就是人類社會權(quán)力和歷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種最大限度的會聚體。在城市這種地方,人類社會生活散射出來的一條條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煥發(fā)出的光彩,都會在這里匯集聚焦,最終凝聚成人類社會的效能和實際意義。所以城市就成為一種象征形式,象征著人類社會中種種關(guān)系的總和:它既是神圣的精神世界——廟宇的所在,又是世俗物質(zhì)世界——市場的所在;它既是法庭的所在,又是研求知識的科學(xué)團體的所在。
城市這個環(huán)境可以促使人類文明的生成物不斷增多、不斷豐富。城市這個環(huán)境也會促使人類經(jīng)驗不斷化育出有生命含義的符號和象征,化育出人類的各種行為模式,化育出有序化的體制、制度。城市這個環(huán)境可以集中展現(xiàn)人類文明的全部重要含義;同樣,城市這個環(huán)境,也讓各民族各時期的時令慶典和儀式活動,綻放成為一幕幕栩栩如生的歷史事件和戲劇性場面,映現(xiàn)出一個全新的、而又有自主意識的人類社會。
古往今來多少城市都是大地的產(chǎn)兒。它們都折射出農(nóng)民征服大地時所表現(xiàn)的勤勞智慧。農(nóng)民翻耕土地以求收獲作物,農(nóng)民把畜群趕進圍欄以求安全,農(nóng)民調(diào)來水源以求滋潤田禾,農(nóng)民建造谷囤糧倉以求存儲收獲物……所以,從技術(shù)的角度看,城市不過是把農(nóng)民營造大地的這種種技能統(tǒng)統(tǒng)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城市就是這種安居樂業(yè)生活的一種象征,這種生活是隨著永久性農(nóng)耕園地的形成而開始實現(xiàn)的:只有當(dāng)有了永久性的庇護所、永久性的生產(chǎn)手段和生產(chǎn)形式的時候——比如果園、葡萄園和灌溉設(shè)施,以及永久性的保存和儲藏手段設(shè)施——人類才形成了這種安居樂業(yè)的生活方式。
鄉(xiāng)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對城市的誕生和存在有所貢獻。農(nóng)民、牧人、樵夫、礦工們的知識經(jīng)驗,都會通過城市轉(zhuǎn)化成為——或者“升華”成為——豐富多彩的成分而在人類文明遺產(chǎn)中流傳久遠:這個人貢獻了紡織品和奶油,那個人貢獻了壕溝、堤壩、木制水管和制陶旋床,第三個人又貢獻了金屬制品和珠寶首飾,等等;這些經(jīng)驗最終都轉(zhuǎn)化成為城市生活中的各種要素和手段。這些東西也增強了城市生活的經(jīng)濟基礎(chǔ),為城市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技藝和智慧。
來自不同疆域、不同部族、不同類型的生產(chǎn)方式當(dāng)中最為精華部分,都會在城市環(huán)境中得以濃縮,這些東西因而才更有可能彼此進行交融和實現(xiàn)新的組合。最終這種城市效能,在它們原來各自狹小而孤立的誕生環(huán)境中是根本無從實現(xiàn)的。
古往今來多少座城市又無一不是時間的產(chǎn)兒。城市是一座座巨大的鑄模,多少人終生的經(jīng)驗積累都在其中冷卻著、凝結(jié)著,又通過藝術(shù)手段被賦予永恒的形式;否者的話,多少歷史事件對于今人根本無從知曉,更談不上延續(xù)和推陳出新,談不上感召更多的人繼續(xù)廣泛參與。
在城市環(huán)境中,時間變得可以看得見、摸得著。建筑物、紀(jì)念碑,以及公共要道、大街小巷,樣樣都比書寫的文字記載更加公開而真實,樣樣都比鄉(xiāng)村里分散的人工物更容易被大眾觀察到、注意到。甚至對于那些很無知、很冷漠的人們,城市的種種影像也會在他們的心目中留下生動印象。
歷史文化遺跡的保護已經(jīng)是當(dāng)今城市中一項重要事實。歷史文化遺跡遺產(chǎn)一代代保護下來了,時間就會向時間挑戰(zhàn),時間就會與時間發(fā)生沖撞;以往歷史上的各種文化習(xí)俗、價值觀念、生活理想,都因此流傳到來世;于是乎,城市以不同的歷史時間層次把一個個世代的具體特征都依次貫穿了起來。就這樣連續(xù)積累,一層疊一層,以往的時間記錄不斷積存在城市之中,直至城市生活本身都感到透不過氣的威脅;于是乎,純粹出于保護的目的,現(xiàn)代人發(fā)明了博物館。
設(shè)想,若離開了城市的豐富時間結(jié)構(gòu)特征,城市自身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逃脫那種“唯有現(xiàn)在”的悲慘局面嗎?如若沒有城市在時間上的豐富性,城市就只能面臨一種單調(diào)的未來,就只能聽到歷史上聽過多次的單調(diào)音響節(jié)奏在未來的乏味重奏。而事實上,城市通過自身以時間和空間合成的豐富而復(fù)雜的交響變奏,一如通過城市中社會勞動分工協(xié)作,城市給自己的生活賦予了交響樂般的品格:各種專業(yè)化的人類才俊,各種專業(yè)化的樂器手段,產(chǎn)生了洪亮的和聲效果,這效果是任何單一器件都無法單獨做到的,無論是音量或是音質(zhì)上。
古往今來多少城市又莫不緣起于人類的社會需求,同時又極大地豐富了這些需求的類型及其表達方法。在城市的作用下,遠方傳入的各種社會力量和影響同本地的同類物質(zhì)相互交融。與它們的融合和諧相比,它們之間的沖突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在城市當(dāng)中,通過市場、聚會場所等介質(zhì)的交融手段的濃縮強化,人類的生存方式逐漸形成了各種替代形式:鄉(xiāng)村中根深蒂固循規(guī)蹈矩淺淺地不再具有強制性,祖?zhèn)鞯纳钅繕?biāo)漸漸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需求滿足;異國他鄉(xiāng)到來的男男女女,異國他鄉(xiāng)傳入的新奇事物,聞所未聞的神靈仙子,無不逐漸瓦解著血緣紐帶和鄰里聯(lián)系。一艘遠方的帆船駛?cè)氤鞘型2矗恢恢获橊勆剃爜淼匠鞘行ⅲ伎赡転楸镜孛椢飵硇氯玖希铺展さ牟捅P帶來新奇的釉彩,給長途通信帶來其所需的新式文字符號體系,甚或還會帶來有關(guān)人類命運的新思想。
城市環(huán)境中,機械學(xué)方面的每一次新奇的應(yīng)用發(fā)明都會產(chǎn)生相應(yīng)的社會結(jié)果;因為機械學(xué)方面的發(fā)明才能和成果,往往引發(fā)新的社會需求;而這些新需求會促使產(chǎn)業(yè)和政府尋求新途徑進行試驗。比如,起初,人們需要建造一處共同設(shè)防的據(jù)點作為庇護所,以抵御猛獸侵襲,這種需求就把本地的鄉(xiāng)村住民吸引到山坡上的堡壘要塞中來居住了。他們在求得共同防御效果的同時,就要將自己混同于其他群體。起初這是迫不得已的,但久而久之,相互交往,以至廣泛合作的可能性都因此大大增加。這種實際過程促使獨自隱匿、巢穴般安謐的鄉(xiāng)村逐步過渡到統(tǒng)一化管理的城市,于是人類有了更高的成就空間,更遠大的發(fā)展前途。
至此,各種經(jīng)驗集體共享的結(jié)果,加上理性批判的激勵,就把鄉(xiāng)村社會中重大儀式和節(jié)日慶典轉(zhuǎn)化為更富有強大想象力的悲劇形式:經(jīng)驗不僅僅被深化了,并在這個過程中被廣泛地傳播開來。同時,在另外的某個平原地區(qū),金匠們原來施用于珍貴物品的消極儲藏方式,則在城市社會壓力和市場機會的雙重作用下,逐漸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強有力的工具手段——銀行,它既借出資金又儲蓄資金,把資本投入流通領(lǐng)域,并最終主宰了貿(mào)易和生產(chǎn)的全過程。
城市是自然界萬般事物事實中的一種,從這個概念上來說,它與一處洞穴、一串游弋的青魚或者一座蟻冢,并無差別。但是,它同時又是一座有靈性的藝術(shù)品,在他共享的社會框架內(nèi),包含有眾多比較淳樸、比較個性化的藝術(shù)形式。人類的精神思想是在城市環(huán)境中逐漸形成的,反過來,城市的形式又限定著人類的精神思想:因為空間——像時間一樣——同樣在城市環(huán)境中被藝術(shù)化地予以重新安排著:城市的邊界線的走向,天際線上城市剪影的高低錯落,地平線上城市形象的低定位及高聳峰巔……這樣,通過對自然空域的取取舍舍,城市就把某個歷史文化和某個歷史時代,各自對于這座城市的存在這一基本事實曾經(jīng)采用過什么態(tài)度,統(tǒng)統(tǒng)記錄了下來:建筑物的蒼穹、尖塔,軒敞的大道,幽秘的庭院,都講述著這樣的故事,不僅講述著城市的各種不同的物質(zhì)設(shè)施,還講述著有關(guān)人類命運的各種不同觀念和思想。
所以,城市既是人類解決共同生活問題的一種物質(zhì)手段;同時,城市又是記述人類這種共同生活方式和這種有利環(huán)境條件下所產(chǎn)生的一致性的一種象征符號。所以,如同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語言本身一樣,城市也是人類最了不起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
通過對空間的具體而形象的利用、控制,城市自身不僅負(fù)載了實用的生產(chǎn)活動功能,而且為居民的日常交往提供了場所:城市,作為集體的藝術(shù)作品,它這種經(jīng)常性效能在托馬斯·曼的講話中有很經(jīng)典的論述。
托馬斯·曼在呂貝克城建成周年紀(jì)念的慶典儀式上的講話中曾經(jīng)說:……一旦城市不再是藝術(shù)和秩序的象征物時,城市就會發(fā)揮一種完全相反的作用,它會讓社會解體,令碎片化的現(xiàn)象更為泛化。試想,在城市的密集雜亂的居住區(qū)之中,各種罪孽和缺德的惡行會傳播得更快;而在城市的石頭建筑物上,這種反社會的事實會牢固地滲透進去,而不會被輕易抹掉:發(fā)生這種情形不是城市生活的光榮,這種光榮曾經(jīng)喚醒了一些圣賢、先知的憤怒,如耶利米、薩佛諾羅拉、盧梭和英國19世紀(jì)的藝術(shù)評論家、社會改革家拉斯金等人。
那么,又是什么東西把鄉(xiāng)村生活中的消極的農(nóng)業(yè)制度轉(zhuǎn)變成為城市生活中的積極體制的呢?城鄉(xiāng)二者的差異不僅僅是人口數(shù)量和密度的差別。因為這其中任何因素都可以發(fā)揮積極的媒介作用,促使本地的交往活動擴大到外地,促使它們必須與外界聯(lián)合、合作、交流、溝通,并形成共同意志:而且,任何一種因素都可以為不同家庭、家族和職業(yè)團體創(chuàng)造成一種潛在的共同行為模式,一種共享的物質(zhì)結(jié)構(gòu)形態(tài),最終使得這些家族、家庭和社團夠成了城市。
這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機會和活動,在基于傳統(tǒng)標(biāo)準(zhǔn)和日常面對面接觸交往的首屬群體之上,又疊加了次級群體的更為職業(yè)化的功能和更為功利性利益;而對于刺激群體來說,它的目的不是固有的,而是有選擇性的,它的成員資格和活動也是具有選擇性的,也正因為如此,這種群體無時無刻不產(chǎn)生著專門化和社會分化的效應(yīng)。
歷史地看,人類文明經(jīng)過自狩獵文化向農(nóng)耕文化的過渡,人口增加,有可能促成了鄉(xiāng)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zhuǎn)變:貿(mào)易通道的拓展,以及職業(yè)種類的增多,又都有可能發(fā)揮促進作用。但是,僅僅從城市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層面是沒有辦法去發(fā)現(xiàn)城市的本質(zhì)的。因為,城市更主要的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新事物。
城市的標(biāo)志物是它那目的性很鮮明的、無比豐富的社會構(gòu)造。城市體現(xiàn)了自然環(huán)境人化,以及人文遺產(chǎn)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賦予前者(自然環(huán)境)以人文形態(tài),而又以永恒的、集體形態(tài)使得后者(人文遺產(chǎn))物化或者外化。
因此,英國生物學(xué)家、社會學(xué)家、區(qū)域規(guī)劃的先驅(qū)人物之一,格迪斯和布蘭德福都曾經(jīng)指出:“關(guān)于城市,一個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實是,城市,作為一種社會器官,通過它的運行職能實現(xiàn)著社會的轉(zhuǎn)化進程”。
城市積累著、包蘊著本地區(qū)的人文遺產(chǎn),同時又以某種形式、某種程度融會了更大范圍內(nèi)的文化遺產(chǎn)——包括一個地域,一個國度,一個種族,一種宗教,乃至全人類的文化遺產(chǎn)。
因此,城市的含義一方面是一個個具有個性的城市個體——它像是一本形象指南,對你講述其所在地區(qū)的現(xiàn)實生活和歷史記錄;另一方面,總括而言,城市又成為人類文明的象征和標(biāo)志——人類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個性的具體城市構(gòu)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