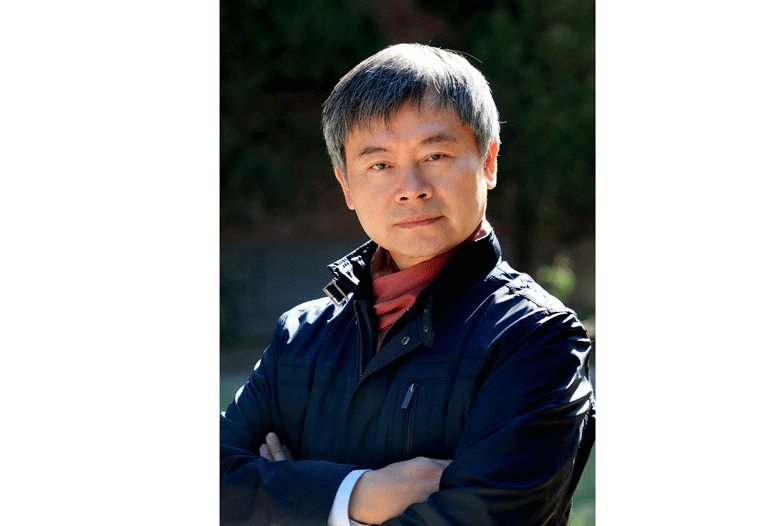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會像中國一樣擁有那么多無證小販,而且他們隨時與城市管理者發(fā)生著各種各樣的沖突。
“追求更為便捷或更好生活是人本能,當(dāng)鄉(xiāng)村與城市之間差距甚大時,人們自然會涌向城市。”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wǎng)中國觀察專欄前學(xué)者高嵩說,“社會資源過度集中于城市,是中國長期二元社會體系下所形成。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漫長歷史上,城市不發(fā)達(dá)也是重要因素,這種上千年的歷史欠債要在短期內(nèi)改變,矛盾的累計自然不可避免。”
中國今天正在經(jīng)歷的著西方社會曾經(jīng)的巨變陣痛,但也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挑戰(zhàn)——如此多的人口,要在如此短時間希望實現(xiàn)城市化。北京大學(xué)電子政務(wù)研究院院長楊鳳春表示,種種情況體現(xiàn)出了中國現(xiàn)實社會的尷尬,因為許多呼吁和建議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與實踐,或者說政府似乎一直對這些問題束手無策。
“魚笱效應(yīng)”加劇城鄉(xiāng)差別
一條條溪澗、一道道山梁……鎖住了鄉(xiāng)村與外界的溝通交流,也鎖住了當(dāng)?shù)乩习傩罩赂坏拈T路。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是云南省會昆明市下轄的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勞動力大縣,其擁有大約20萬勞動力,其中7~8萬為富余人員。
“2011年全縣的勞動力輸出任務(wù)是2.3萬人,至4月底已經(jīng)完成了9800多人。”祿勸縣農(nóng)民就業(yè)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錢衛(wèi)東說,“在本地沒有更多的企業(yè)吸收勞動力的情況下,他們出門打工,進到城市用各種方法賺錢的情況很難改變。”
位于滇川交界的祿勸,縣域道路交通建設(shè)起步晚,基礎(chǔ)設(shè)施薄弱,直接制約著經(jīng)濟發(fā)展。雖然2006年以來祿勸縣也達(dá)到了鄉(xiāng)鄉(xiāng)通油路,道路狀況得到一些提升,但建制村道路面臨著許多嚴(yán)峻考驗。盡管昆明市在“十一五”道路實施方案中將祿勸道路建設(shè)的直接補助提到85%,但需要縣自籌的15%也很難完成,造成村級公路建設(shè)存在嚴(yán)重資金不足,很多項目得不到實施。
事實上,基礎(chǔ)設(shè)施薄弱是制約西部貧困地區(qū)發(fā)展的重要“瓶頸”,行路難、用電難、飲水難、通訊不暢等問題還比較突出,因此規(guī)劃中的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shè)都要涉及飲水、架電、修路、文化、公益事業(yè)等。
錢衛(wèi)東表示,云南全省幾乎都有著同樣的情況,如果農(nóng)民們能夠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去找工作,而不需要政府幫助當(dāng)然最好,但是情況不可能是這樣,他們對政府既信任、又依賴,“有一點需要說清楚,政府所組織出去的勞動力,基本都是進到工廠、企業(yè)有秩序地上班,沒有一例是讓他們?nèi)コ鞘欣飻[小攤,做無證小生意的,同時有許多小販原本就是城市里的窮人”。
“一些人之所以到了城市里會成為小販,其實還是因為文化低、能力差,缺乏競爭意識,比如在我們本地搞工程、開辦企業(yè),都很難招到有技術(shù)的工人,再提高工資都不行。”錢衛(wèi)東說,“擺無證小攤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當(dāng)他們意識到這樣做比打工更自由、更賺錢時,很可能會辭掉原來的工作加入這個行列。其實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合法經(jīng)營,的確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個別也包括沒有這樣的意識。”
高嵩表示,拉美國家那些巨型貧民窟容納的更多是來自鄉(xiāng)村的移民,在中國這種故事每天都在重復(fù),因技能和教育的差異,相當(dāng)多的外來者只能在城市的邊緣尋找生活的空間,“即便是在紐約、香港那樣的國際化城市,‘走鬼’也從未被消滅”。
從上世紀(jì)80年代初開始,祿勸縣勞動就業(yè)部門就開始引導(dǎo)農(nóng)村青年走出家鄉(xiāng),希望使過去“輸血”式扶貧變?yōu)椤霸煅笔椒鲐殻?0多年來,不僅創(chuàng)造了40個億的勞務(wù)收入,還開拓了農(nóng)民的視野。其中,由政府部門輸出的人數(shù)只占30%左右,即潛在的經(jīng)濟價值還很大。
2005年,祿勸縣獲得昆明市勞務(wù)輸出綜合考核第一名,但一名縣領(lǐng)導(dǎo)表示:“拿第一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說明我們的經(jīng)濟不發(fā)達(dá)。”錢衛(wèi)東認(rèn)為,在特定歷史時期,政府必須主導(dǎo)勞動力輸出工作,但未來經(jīng)濟發(fā)展了,政府就應(yīng)該回歸到勞動維權(quán)和創(chuàng)建良好用工環(huán)境的本位上。
長期關(guān)注中國鄉(xiāng)村問題的學(xué)者熊培云認(rèn)為,在城市化、現(xiàn)代化背景下,農(nóng)家子弟大量進城,此為大勢所趨,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必然導(dǎo)致鄉(xiāng)村衰敗,問題的關(guān)鍵還在于它沒有一個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單向流動”,這是一種“魚笱效應(yīng)”(一種頭大尾小、中間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魚簍);作為個體,農(nóng)家子弟能夠遠(yuǎn)走他城,救起自己甚至大家庭,卻無法救起自己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難回,正是源于“魚笱效應(yīng)”不斷加劇城鄉(xiāng)之間的差別,并促成鄉(xiāng)村的整體性衰敗。
祿勸縣皎平渡鄉(xiāng)加貢村的阮天翠說:“農(nóng)村怎么也不可能超過城市,雖然現(xiàn)在政府對農(nóng)村的關(guān)心也很多,但是仍然不能與城市相比。如果農(nóng)村的交通、醫(yī)院和學(xué)校等條件能夠達(dá)到城市一半,我相信很多人就不會愿意出門打工了。”祿勸縣許多外出打工的農(nóng)民這樣解釋著自己的舉動:“城市里工作機會、學(xué)校和醫(yī)院都多,房子、商店和街道都非常漂亮,農(nóng)村里幾乎什么都沒有。”“
熊培云稱,由于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剪刀差、農(nóng)村稅收和支農(nóng)支出收付相抵缺口、不合理征地以及針對農(nóng)民工的歧視性待遇等城鄉(xiāng)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國農(nóng)民每年向城市輸出兩萬億元的“貢獻(xiàn)”。
“城市變成了‘抽血機’,只從鄉(xiāng)村抽取養(yǎng)分和年輕人,但很少進行反哺和滋養(yǎng),甚至連一個老人也不回饋給它。200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由于醫(yī)療服務(wù)保障的城鄉(xiāng)差異,中國大城市的人均壽命比農(nóng)村高了12年。僅此一項福利,就足以決定大多數(shù)有還鄉(xiāng)之愿的人繼續(xù)住在城里。”
集中力量辦大事?
“如果能有一份好工作,沒人愿意這樣風(fēng)吹日曬,還被城管攆來打去。”類似的話語從許多有思考和表達(dá)能力小販中經(jīng)常聽到。
1998年起一直從事小攤販行當(dāng)?shù)哪暇┚W(wǎng)民“批評家老趙”表示,小攤販小買賣都是貧窮致富的“支點”,是失敗者的緩沖帶,無商不富無富不危是個客觀規(guī)律。
“小攤販表面上看起來比較自由賺錢容易,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痛苦的工作,城管、保安、衛(wèi)生、街道、店鋪老板、黑惡勢力都要管,有時警察也管,還經(jīng)常看顧客臉色,有人管沒人保護,面臨著體力和心靈雙重傷害,所以小攤販的眼神總是充滿了恐懼和憔悴。”他感慨。
“我認(rèn)為未來中國的城市還會越來越大,這與整個國家的發(fā)展思路有關(guān)。”錢衛(wèi)東說,“現(xiàn)在全國都有一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指導(dǎo)思想,具體到地方發(fā)展就是要先建好各種中心城市,然后再對周邊、對農(nóng)村產(chǎn)生輻射和帶動作用。”
他表示,按照這樣的發(fā)展思路,短期內(nèi)勞動力還是大量要往大城市、中心城市會聚,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肯定會成為小商販。
祿勸縣皎平渡鄉(xiāng)太平村16歲的祝麗說:“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都愿意出門打工,既能掙錢又能學(xué)本事,而且他們絕大部分都去了工作機會更多的昆明。”
楊鳳春認(rèn)為,成為城市人和貌似城市人是許多中國農(nóng)民的夢想,因為1949年以后的二元制格局致使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這樣的情況并非自然的結(jié)果,而是政策強力導(dǎo)向所致;如果說上個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國家的發(fā)展還有些“發(fā)展面”的概念,但八十年代以后基本就是“發(fā)展點”的現(xiàn)實了,后者例如深圳、廣州、北京和上海等,政策導(dǎo)向決定了它們能夠積聚大量的高端資源,而其他的地區(qū)發(fā)展卻屢屢受到各種制約。
“中國農(nóng)村不發(fā)達(dá)與城市里發(fā)生的這些矛盾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在中國人的人性、國民性沒有發(fā)生改變改變之前,大量農(nóng)民其實是被逼出門的,因為城市文明、現(xiàn)代文明都是農(nóng)村里沒有的,也缺乏賺到現(xiàn)金的機會,農(nóng)民們對城市普遍存在一種既羨慕、又嫉妒的心態(tài)。”
有學(xué)者認(rèn)為,要解決好“三農(nóng)問題”必須“提高農(nóng)民人均收入,主要出路是減少農(nóng)民占總?cè)丝诘谋壤醋屴r(nóng)民進城”。不過,中國到底要不要讓更多農(nóng)民進城和大力推進大城市化,長期以來似乎也是一種沒有定論的爭議。
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由于外出的農(nóng)民越來越多,全國各地產(chǎn)生了很多“空心村”、“老少村”,即平時已經(jīng)沒有多少農(nóng)民居住,或者只有老弱病殘在居住,村莊面積很大卻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浪費和閑置了很多土地。錢衛(wèi)東證實:“這樣的情況并非危言聳聽,比如我經(jīng)常到一些農(nóng)村里上課培訓(xùn),看著講臺下面很少有青壯年,同時大家精神面貌不佳的情況,總覺得很心酸。”
熊培云認(rèn)為,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都會加大投入補貼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而在過去相當(dāng)長的時期,中國農(nóng)民不但得不到補貼,而且還要不斷為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城市化輸血。即使近些年中國經(jīng)濟有了較好的發(fā)展,政府對農(nóng)民的補貼依舊捉襟見肘。2005年世界經(jīng)濟合作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政府補貼給本國農(nóng)民的錢只占本國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6%,而歐盟諸國平均是34%,美國是20%,日本是58%,韓國是64%。
“現(xiàn)有的不合理制度造成所有優(yōu)勢資源都集中在城市里,因參軍、入學(xué)及打工等導(dǎo)致農(nóng)村精華大量持續(xù)外出不歸,只剩下‘386199部隊’(指婦女、小孩和老人)。”他說,“鄉(xiāng)村精英的流逝,政治上的不設(shè)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鄉(xiāng)發(fā)展的嚴(yán)重失衡,都是鄉(xiāng)村衰敗的重要原因,背后的局面就是有想法、有能力的農(nóng)民紛紛進城。”
可變因素
據(jù)熊培云觀察,中國與歐洲等國家的差別,除了體制之外,最主要仍在于鄉(xiāng)村社會的面貌及其是否可以作為家園繼續(xù)存在。眾多努力和變化集合在一起,所產(chǎn)生的力量會扭轉(zhuǎn)目前“農(nóng)民大量進城做小販,城管暴力對付小販”等尷尬局面。”萬物消長,一些新鄉(xiāng)村社會同時正在形成。最終應(yīng)當(dāng)使農(nóng)民是為選擇想要的生活而非只是為了謀生而逃向城市。
但在楊鳳春看來,現(xiàn)在中國的城市問題遠(yuǎn)非城鄉(xiāng)制度不平衡那么簡單,可以說已經(jīng)形成了一些能夠左右國家政策的利益集團,如果不把優(yōu)勢資源集中在少數(shù)地方,而是公平分配城鄉(xiāng)各地,那么現(xiàn)有的龐大利益就會消失,利益集團肯定不會輕易答應(yīng)。
“中國有著特殊的國情,不可變的因素不要硬闖,但可變因素也存在。由于現(xiàn)在管理城市的官員基本都是30年前接受的高等教育,除了所有城市都是一樣的面孔,官員們對城市管理的方法也大同小異,因此城管與小販的沖突隨處可見,很少有例外的地方。城市怎么管要由大家而不是市長說了算,教育、培訓(xùn)現(xiàn)有市長的水平和修養(yǎng)也是可行的。除了要求他們不再像小包工頭,每天做些拆遷、重建,沒有多少技術(shù)、智慧含量的工作,更要消除那種沒有文化多樣性、沒有歷史感,盲目崇洋媚外的城市建設(shè)異相。”
“批評家老趙”認(rèn)為,許多人錯誤地認(rèn)為“城管”是上個世紀(jì)90年代新型的產(chǎn)物,事實上自古以來就有這個部門存在,只不過每個時期的叫法不一樣,新中國成立以后起先在各個城市里組織起來的“工人糾察隊”就是現(xiàn)在“城管”的前身。他表示:“翻開中國古代史可以看到的禁令太多,唯一就沒有禁過做小買賣的,然而在近代歷史上就連續(xù)兩次,一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二是現(xiàn)時代。”
“中國的城管現(xiàn)象在世界范圍內(nèi)應(yīng)該是特例,其是被推到第一線的執(zhí)行者,背負(fù)著巨大的行政壓力。”高嵩說,“當(dāng)城市要靠暴力來維護它的光潔時,人們有理由懷疑,這樣的城市能否誕生令人溫暖的文化與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