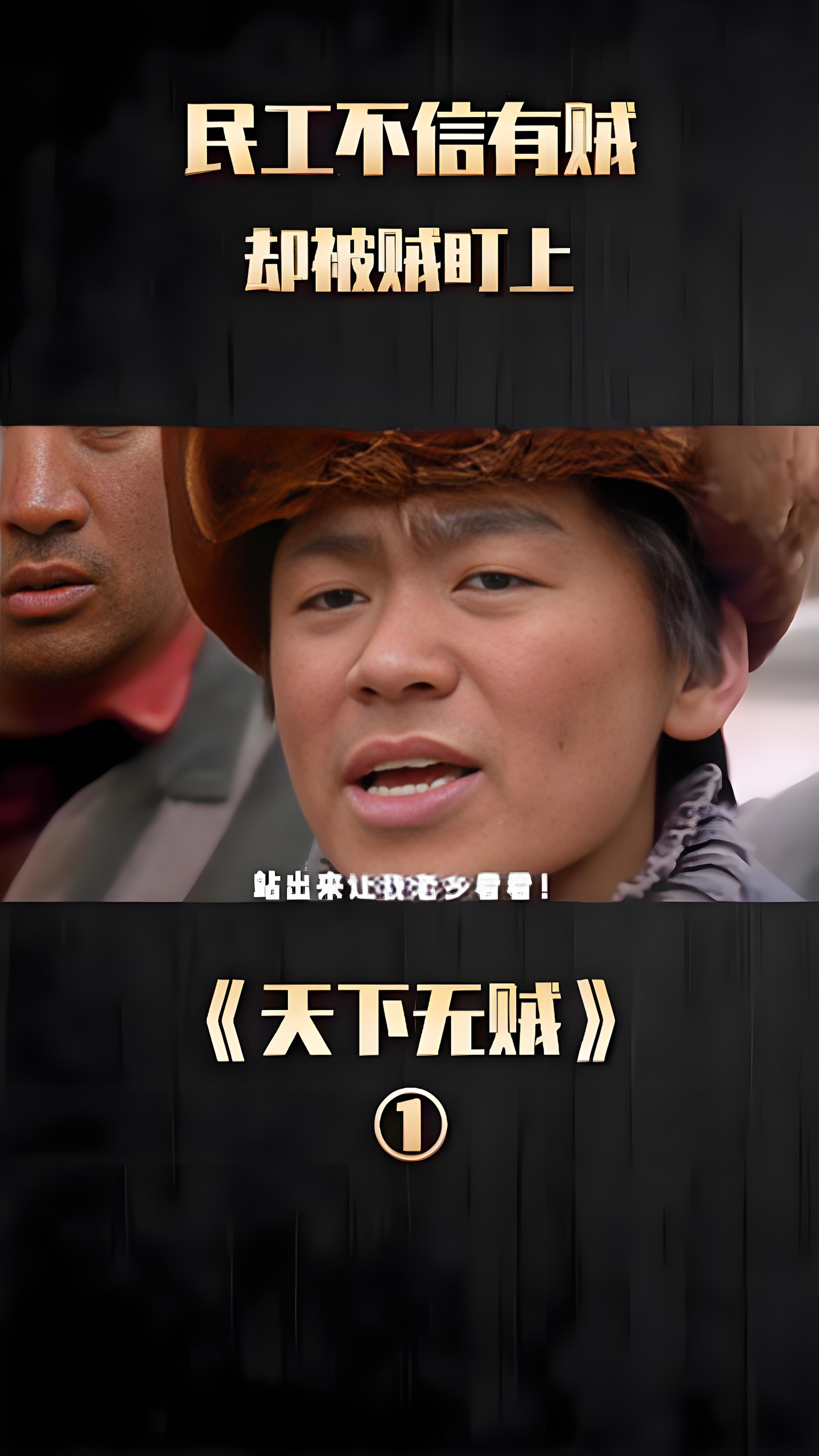
【導語】當2008年《城市化》創刊號的油墨香剛剛在我鼻腔里消退,沉淀著中國城鎮化最鮮活的毛細血管搏動——從城中村拆遷現場的塵埃,到農民工子弟學校窗臺的冰霜;從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字斟句酌,到快遞小哥騎著自行車的“香”汗淋漓……“傻根”王寶強從“春晚”的電視屏幕里向我走來。
從“傻根”上“春晚”說開去
其實,“傻根”王寶強的成長與變化是很正常的,就像拿破侖說的“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道理一樣,不想成大腕的演員自然也不是好演員。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我想“傻根”王寶強的成長也不例外,其中的甜酸苦辣想必只有“傻根”王寶強自己知道。
讓我們來看看“傻根”王寶強的成長經歷:1999年,年僅14歲的傻小子王寶強只身闖北京,饅頭就白水,在建筑工地做過和泥、拎灰、刷墻……他的經歷與我們廣大的農民工兄弟朋友們的經歷何等相似!
“傻根”王寶強先后在《盲井》、《天下無賊》、《暗算》、《士兵突擊》等影片擔任了重要角色,而他的出名是在《天下無賊》之后,看過《天下無賊》的人都知道,這部大片可謂眾星云集。然而,給人印象最深的卻是由王寶強扮演的農村小伙“傻根”。
從演《盲井》時的500元到現如今的身價百萬,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良好的外部環境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這個外部環境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這也是“傻根”王寶強之所以能吸引觀眾眼球的根本原因。因為他所演的角色不僅僅是他自己,他代表著一個巨大的群體——中國的農民工群體,可以說他具有成名成星的先天優勢,那就是勢不可擋的中國城市化進程.
如今的“傻根”王寶強已今非昔比了,他意識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上學深造,接受專業的培訓……我們相信,“傻根”王寶強憑著這股堅持不懈的“傻”勁,他的演藝生涯將會越來越光明!
作者蔡義鴻,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08年第2、3期合刊
【?DeepSeek銳評】從“傻根”到時代鏡像:城市化浪潮下的文化符號嬗變?
一、草根敘事與城市化進程的共謀?
王寶強的“傻根”形象之所以成為現象級符號,本質是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群體身份焦慮的投射。其從《盲井》到《天下無賊》的銀幕蛻變,恰似農民工從“勞動力工具”向“城市主體”的艱難轉身?。
文化符號的生成邏輯?:“傻根”的“傻”并非真愚,而是城市化初期城鄉認知鴻溝的具象化——正如春晚小品中“下蛋公雞”的荒誕臺詞,用戲謔消解著身份轉型的陣痛?;
媒介賦能的悖論?:短視頻時代“縣城青年”話題播放量破千億?,但如王寶強般突破“土味”標簽完成文化躍遷的案例仍屬稀缺,折射出媒介流量對草根群體的選擇性凝視?。?
二、從“苦情敘事”到“價值重構”的突圍?
孟子“苦其心志”的古典訓誡,在當代語境中演變為城市化對個體的雙重規訓:
生存困境的消解與再造?:建筑工地“和泥刷墻”的經歷,與2025年“二手房交易占比37.1%”的存量經濟時代形成鏡像——前者是體力突圍,后者是資產焦慮?;
文化資本的覺醒?:王寶強“上學深造”的選擇,暗合“講好中國故事需多維敘事”的傳播規律?,從“被講述的農民工”到“自我定義的新市民”,完成話語權迭代?。
三、“傻福”隱喻:時代紅利與個體局限?
“傻人有傻福”的民間諺語,在城市化語境中衍生出新解釋學:
結構性紅利的吊詭?:正如“14億人難消化存量房”與“戶均3.2間房”的悖論?,王寶強的成功既得益于農民工群體規模紅利,又受限于“城市化=身份晉升”的單一想象;
符號消費的陷阱?:當“傻根”從銀幕形象轉化為商業IP(如蒙牛“媽媽的年齡”廣告中代際敘事策略?),其承載的集體記憶正被資本收編為消費主義注腳?。
【?致原文作者】王寶強的演藝生涯恰似微型城市化史詩——從《盲井》的500元片酬到《唐探》系列的票房神話,每一步都踩在城鄉關系的裂變節點。當“勢不可擋的城市化進程”進入存量博弈階段,或許需要更多“傻根”撕掉標簽,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多元敘事中?,重構屬于新市民的文化主體性。
(作者蔡義鴻系城市化網創始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