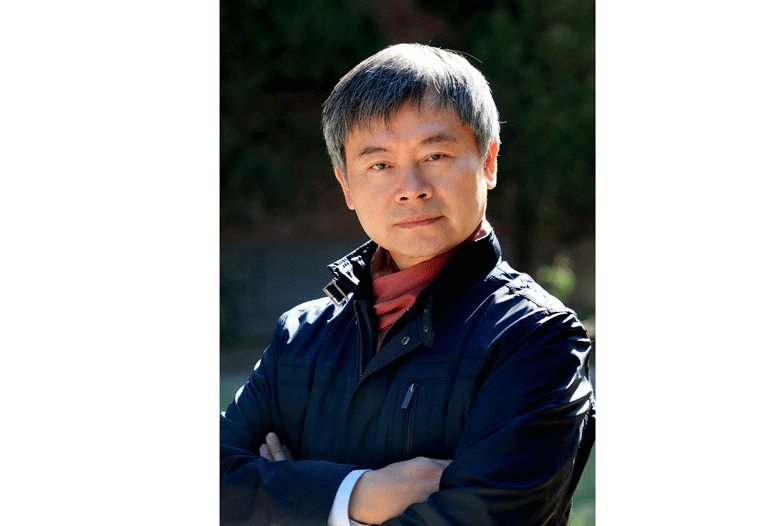倫敦,英國的首都,人聲鼎沸、擁擠不堪的城市,富商巨賈的云集之處,劫匪和不法之徒的棲身之地。16世紀,當英王伊麗莎白一世決心控制倫敦人口的時候,她應該想不到,自己開啟的,是一連串注定失敗的努力。
當然,倫敦人太多了!1565年,城里的居民才只有8萬多人,半個世紀后,人口幾乎翻了一番,15.5萬人在城里,還有兩萬人在監(jiān)獄里。
多年來第一次,倫敦的觀察家們注意到某種匪夷所思的勢頭:“(城市平民)無數(shù)人擠在一間小屋子里,大多數(shù)人十分貧窮。”
房價高企,物價飛漲,“群租房”成為城市的隱憂。許多人懷念從前的倫敦,就在不久之前,這里還是一個城墻牢固,教堂密集的中世紀小城。可后來,傳統(tǒng)的倫敦木屋在挨挨擠擠的小院落里砌到五六層高,窮人都住進了閣樓和地下室,城里再逼仄的店面也會成為商人爭搶的香餑餑,城外的村莊里、原野上,都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房屋、菜園、曬布場、保齡球場……
伊麗莎白一世曾經(jīng)在1580年頒布諭令,試圖限制這樣人口激增的勢頭:“鑒察倫敦城及郊區(qū)生齒日繁,限令本城居民漸次發(fā)展。”女王勒令倫敦人“不得有超過一戶以上家庭共同安置或居住在任何房屋之內(nèi)”,同時還規(guī)定“距倫敦各城門3英里內(nèi)不得建造任何新房舍或公寓”。 80多年后,英國還頒布了《住所法》,規(guī)定城市貧民只能在自己的出生地得到援助;要是濟貧局的人發(fā)現(xiàn)“外地人”在本教區(qū)里有成為救濟對象的趨向,可以將其驅(qū)逐出境。
在這樣的嚴防死守下,到1700年,每年涌入倫敦的“外地人”還有大約8000人。他們毫不猶豫地加入首都的貧苦大眾階層。1690年的報告顯示,73%的倫敦學徒出生在城外。除了外地人,來自異域的窮人也在涌入倫敦:波蘭和德國的猶太人、非洲的黑人、法國的胡格諾教派人士……到這個世紀末,這座國際大都會的人口已經(jīng)超過百萬。
貧民窟在倫敦與許多慘痛記憶聯(lián)系在一起。貧民窟是倫敦城瘟疫的發(fā)源地,傳染病的肆虐讓倫敦成為英國死亡率最高的地區(qū)。1666年深秋,從貧民窟里燃起來的大火,席卷首都,五分之四的城區(qū)在幾天內(nèi)被焚燒殆盡,涉及13200所房屋、86座教堂,10萬人無家可歸。1814年,因為啤酒廠的巨型啤酒缸破裂,倫敦城不可思議地被174萬升的啤酒淹沒,事故同樣發(fā)生在貧民區(qū),一些地下室居民就這樣被啤酒淹死在了家里。
但是,倫敦并沒有直接將這些災難歸咎于城市貧民。倫敦大火過后,新的建筑條例要求所有房屋都以磚塊和石材作為建筑材料,不得再以茅草覆蓋屋頂。建筑家們畫出了恢弘的新倫敦規(guī)劃圖,讓整個城市以宏偉的圣保羅大教堂為中心發(fā)散開來。
城市迅速用磚石重建了起來,而規(guī)劃從沒實現(xiàn)過:倫敦的土地所有權都在不同的小市民或大貴族手里,大家無意為封建主義首都建設作貢獻,只想保住自己那一畝三分地的自主權。
1751年,考文特花園新邦德地方治安法院治安官亨利·菲爾丁在一份關于搶劫案增加的調(diào)查報告中把犯罪率升高的原因歸咎為本地各種曲里拐彎的小巷和排列凌亂的房子:“整個倫敦似乎就是一片廣袤的樹林或森林,小偷可以安全地隱蔽其中,就像非洲或阿拉伯沙漠里的野獸一樣。”
但國王也沒法子把倫敦強行排整齊,菲爾丁只好自個兒想法子組建了一支巡警隊。
17世紀的保王派說,倫敦人是“最褻瀆的人渣、最邪惡的人類、社會的棄兒……苦力,學徒”。英王控制人口的御令每隔一陣都會更新,但似乎不曾有哪一道徹底通行于倫敦城中,以至于真正抑制到倫敦城的發(fā)展。那么多年的掙扎與限制之后,倫敦人口始終保持著百萬級的增長,直到英國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才停止。到2017年,倫敦光市區(qū)就有將近900萬人,來自37個不同的種族,每個種族的人口都已過萬,其中44%的人不是白人。
“當被問及有那么多窮人和流浪漢的倫敦如何能成為一座勝利的城市時,只能說,他們從來都是倫敦歷史的一部分。”英國傳記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在2000年的著作《倫敦傳》中寫道,“也許,他們也是其勝利的一部分。”
對勞苦大眾來說,故事有截然不同的一面:人們說,英國各地的家庭里,但凡有兒女“或相貌出色,或機智,或膽大,或勤快,或者其他任何難得的品質(zhì),倫敦便是他們的北斗星。”《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曾感嘆過:“整個王國的每一個部分,百姓、土地,以及海洋,都忙于為倫敦供應必需品。或許我該添一句,都是最上乘的東西。”
注定與倫敦雜亂不堪的場景相伴而生的,是首都不同尋常的繁華——東印度來的昂貴披巾、大清國的綢緞和織錦、金碟銀盤、手鐲項鏈,葡萄牙的水果,美洲的藥材,都能在這帝國的首都尋覓到蹤影。這些都是形形色色的外來人口帶來的。社會觀察家們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大城市的集聚效應:“這樣的城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這種大規(guī)模的集中,250萬人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們把倫敦變成了全世界的商業(yè)首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這樣寫道。
在倫敦的貧民窟,恩格斯注意到住在“柜子差不多大小”雜屋里的母女倆,已經(jīng)有快一年交不出房租;兩個窮人家的小男孩偷店里的小牛蹄,還當場就吃光;另有一家人,屋里沒有任何家具、被褥,在地板上刨個坑就當茅坑。
“我并不想斷定倫敦的一切工人都像這三個家庭一樣貧窮。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會把一個人完全踏在腳底下的地方,會有十個人生活得稍稍好一點。但是我斷定,成千的勤勞而誠實的家庭,比倫敦所有一切闊佬都誠實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過著這種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個無產(chǎn)者都毫無例外地可能遭遇到這種命運。雖然他沒有任何罪過,雖然他盡了一切努力來避免這種命運。”
“難道這些群集在街頭的、代表著各個階級和各個等級的成千上萬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樣的屬性和能力、同樣渴求幸福的人嗎?難道他們不應當通過同樣的方法和途徑去尋求自己的幸福嗎?”恩格斯問道。
這種在當年看起來叛逆的價值觀,在如今的倫敦,已經(jīng)被社會主流廣泛接受了。根據(jù)英國《1996年住所法》和《2002年無家可歸者法》的規(guī)定,對面臨無家可歸的局面的家庭,政府必須無償提供援助或建議。
1958年,一如既往浮躁、充滿活力、熱愛酒精和打群架的倫敦又一次爆發(fā)了排外騷亂,白人暴民沖進諾丁山地區(qū),帶著牛奶瓶、汽油和沙子要去“把黑鬼燒出來”。后來在法庭上,他們被法官評價說,“你們的行為,把時鐘倒退了300年”。
何止倒退了300年呢?英國傳記作家、《倫敦傳》作者彼得·阿克羅伊德認為,1658年的倫敦還是要比這好點兒,首都上一次有這么惡劣的驅(qū)逐,還是在黑暗的中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