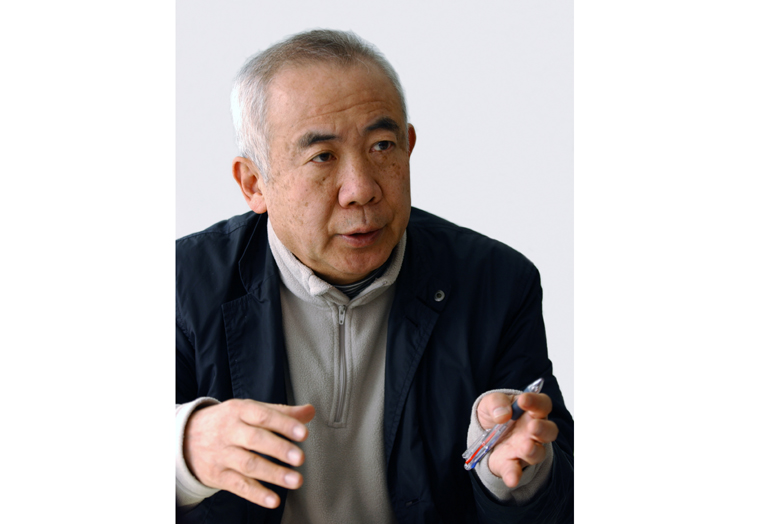作者簡介:
現任職務: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城市經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高級會員、清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城市思想者研修計劃首席學監、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客座教授、深圳市城市化研究會副會長、深圳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等職務。
研究項目:2000年創辦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經營研究中心,主持的城市戰略與城市經營研究咨詢項目有:《漳州市城市化戰略》、《深圳2030年發展策略-城市功能演進與土地經營策略》、《順德新城區發展策略》、《重慶永川市城市化發展戰略》、《山東德州開發區發展戰略》、《深圳市寶安區城中村改造戰略》等。
隨著生態移民下山進城的用地指標,多少有些象過去在食物短缺時“糧票”的作用。現在,建設用地需要總量控制,每個走進城市的生態移民又需要包括住房在內的最低保障,我們不妨建立“地票”,也就是隨著生態移民轉移的用地指標,使得到這些指標的城市具有接受移民的積極性。
生產移民最終應當走進城市
不論是三江源的退牧還草,還是三峽庫區的退耕還林,所由產生的生態移民,其實是當大自然向人類發出生態警報之后,人類自覺地從那些邊際生態壓力最大的地方撤出自己的部分成員,讓他們轉向生態壓力相對較輕的地區。
在同樣的生活質量下,什么地方是人類對自然邊際壓力最小的地方呢?換句話說,什么地方人類的生態足跡相對最小呢?是城市,特別是處于江河下游、沿海地區的大城市。由此來看,推動城市化的動力,不僅是人類成員聚集而產生的經濟效益,還有來自生態的壓力。不僅有一只“亞當斯密之手”,還有一只“馬爾薩斯之手”。
筆者曾經在渝西地區調研中,看到了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有一個鄉鎮接收了64戶288名來自三峽庫區的移民。按照政策,當地政府為每戶移民蓋好了住房,調整出耕地。但是,移民中真正居住下來從事農業的不足10%。剩下的90%,或者是在庫區家鄉的縣城里,或者是到其他的大中城市里去打工了。由于生計的原因,他們選擇了到城市中去打工,而不是定居到我們一廂情愿地為他們安排好的新家園中。這個觸目驚心的事實告訴我們什么呢?
首先,從就業轉型來說,有時候農轉農比農轉非更難。這些移民以往居住在三峽庫區的奉節縣,那里盛產柑桔,擁有幾十萬畝優質的柑桔林。農民所擁有的柑桔種植技術和這片林地結合起來,就可以過上初步的小康生活。但是,當他們面對一片不熟悉的土地,需要從頭學習種糧、種菜時,其難度之大超出我們城市人的想象。有一個移民找到市領導,說我只會種柑桔,能不能為我安排一片柑桔林來種呢?其實,改變種植作業的習慣之難,遠遠勝過他們扛著棒棒走進城市去打工。對于他們來說,城市比起不熟悉的農村更適合生存。
第二,從生態壓力來看,農轉農沒有根本緩解人與自然的矛盾。在前述接收移民的那個地方,農村的人均耕地也只有1畝左右。在這樣的人均耕地水平下,憑著務農,無論如何也奔不到小康。而新增的農業人口又加強了人地矛盾,從根本上推延了這個地區農民脫貧奔康的進程。
第三,從人口遷徙的方向來看,政策的指揮棒偏離了人民群眾的意愿,農民在生態上做出了惠及全市乃至全國人民的貢獻,一無所有地走進城市,卻在不相干的地方就擁有了一塊農地與農宅,結果是政府“頭疼醫腳”,農民“種瓜得豆”。
這種令人痛心的現象背后,隱含的還是城鄉之間的偏見與歧視。城是城,鄉是鄉。鄉村中的移民只能到另外的鄉村去,而不能走進城市。
長期以來,我們就是這樣關起城市的大門搞建設移民和生態移民。在三峽庫區,淹沒線以下的移民或者是就地后退上山,或者是遷移到其他地區的農村。其結果,不僅城鄉矛盾加深,人與自然的矛盾也越發的逼仄。其實,人與自然之間的統籌是五個統籌中最高層次的統籌。區域統籌、城鄉統籌只有服從這個最高層次的統籌,才能找到出路。生態移民最終一定要走進城市,這才是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大原則。因此,我們必須打開城市的大門,接收生態移民。
讓城市樂于接受生態移民
長達60年的和平發展,已經使中國農村地區人口增長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農業生產的邊際收益大大遞減。地處渝東、三峽庫區的一個山區縣里,全縣人口52萬人,耕地45萬畝。但是當我們走進這個縣就可以發現,一方面山青水秀、谷幽澗深,另一方面大量的梯田已經爬上了高山陡坡。全縣的耕地中,大約有三分之一處于25度以上的坡地,是人類超越大自然容許范圍開發的農業用地,最終應該退耕還林。
城鎮的情況又如何呢?1.2平方公里的縣城,已經住滿了4.5萬人。這個縣在撤鄉并鎮中,有的三個鄉合并成一個鄉。然而要在這三個鄉的中間地帶另選新址建鄉政府的時候,縣委書記和縣委辦主任親自下基層,也沒有找到一塊合格的平壩子。最近,縣城里強制拆遷了一百多戶人家,原因是他們居住的地方屬于“巖崩地帶”。在這個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的地方,我看到了人與自然的貼身肉搏。
估算一下,按照糧食的產量與單價,若要達到低水平的小康,農業的規模化至少要求勞均20畝土地。這樣算下來,全縣可以承載的農業人口也就是5萬人。如果全縣所有的鄉鎮能容納15萬的城鎮人口,也就意味著,這個縣的生態承載力只有20萬人,至少應該移出30萬生態移民。其實,在大躍進的1958年,這個縣的人口只有30萬人。因此,既使移出30萬人,剩下20萬人,這個山區的縣也并不是一個生態的烏托邦。
但是,要接受這些生態移民,城市的積極性從哪里來呢?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的城市都不拒絕作為勞動力的生態移民,因為就業自理、吃飯自理、住房自理。城市得到了勞動力所創造的工商稅收,卻不承擔對這些勞動力的社保福利等項公共支出的責任,叫做“經濟吸納、社會拒入”。城市接受了勞動力,卻沒有接受人口,更沒有接受這些人口的其他家庭成員。這就是造成當前經濟城市化超前、社會城市化滯后的根本原因。
如何讓城市不僅樂于接受作為勞動力的生態移民,并且樂于接受作為人口的生態移民呢?這就需要我們跳出城鄉分治的傳統思維,從人與自然的協調出發,將生態區域的保育和城市區域的建設結合起來,將減少庫區的耕地和增加城市建設的用地掛起鉤,讓生態移民帶著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下山進城,使得接收生態移民的城市因為接收移民而獲取新增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這樣一來,在當前嚴格控制城市建設用地的宏觀環境之下,城市有了寶貴的新增建設用地的指標,也就有了主動接收生態移民的積極性。而下山進城的移民也就懷揣著一份指標,富有尊嚴地選擇自己的去向。
關于“地票”的設想
“地票”是指生態移民放棄原有生產和生活用地、走進城市之后,由國家所賦予遷入地的一份城市用地指標。
當前國家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使得全國各地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緊缺,城市用地指標隨著生態移民走,多少有些像過去在食物短缺時“糧票”的作用。當時由于糧食總量控制,每個人又需要最低的食品保障,因而實行了糧票制度。票隨人走,總量控制。現在,建設用地需要總量控制,人則要從生態敏感區退下來走進城市。在土地如此短缺之時,首先要確保作為保障品的供給。這就要建立一種“地票”。糧食與土地相同之處,就在于兩者作為基本生活保障的時候需求彈性極低,“人人有飯吃”和“居者有其屋”一樣都是天賦人權。但是,城鄉二元結構之下,糧票是城市居民的吃糧保障,農民進城沒有糧票需要“自理口糧”,農民進城也要“自理住房”,建設部門所規定的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只有城市戶籍居民才能享受。這樣的制度安排下,進城農民無法得到城市居民擁有的城市住房基本保障,家鄉的住宅用地和耕地也無法流轉。一方面是農民進城不能享受同樣的待遇,另一方面則是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我們需要讓生態移民進城之后也得到住房保障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權益,這就要創制一種跨越城鄉的“地票”,也就是隨著生態移民的流動而轉移的用地指標。生態移民選擇了哪一座城市,也就將國家賦予的用地指標落在了哪個城市,從而換來了在這所城市中的成員權。“地票”制度就是讓接收生態移民的城市在接受政治任務的同時,擁有更多的發展空間。城市為了爭取這種發展空間,就要接納更多的移民作為城市的市民。
長遠地看,當全國范圍內實現城鄉統籌的時候,中國農民從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村遷徙出來,不論是不是通常口徑下的“生態移民”,都是對全國的生態做出一份貢獻,都應擁有在中國城市中一份相應的權益。那時候,“地票”就不僅是生態移民,而是所有農民走進城市時的一張身份證明和一份城市資產了。城鄉統籌也才最終落實到城鄉居民發展權力與機會的兼顧之上。
“地票”政策的操作問題
“地票”的設想要能夠操作,還需要破解一系列的問題:
問題1:從哪里試點?
我國幅員遼闊,在不同的區域里人與自然的矛盾沖突程度不同。總的來說,西部地區生態更脆弱,東部沿海地區生態容量更大。因此,國家需要抓住城市化的大機遇,完成一個全國人口從西向東“移山填海”的過程。但是,東部地區如山東,城市的擴張空間大,生態移民的壓力小;而西部地區比如青海,生態移民的壓力大,而城市擴張的動力有限,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這項統籌會涉及太多的操作困難。
能否在一個省市區之內先作試點呢?這就需要選擇那種同時具有大城市和大農村的地區,負有城鄉統籌責任的政府。我想,最適宜的試點地區應是重慶。重慶一方面,三峽庫區生態脆弱,需要大量的移民搬遷,另一方面,重慶作為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主城為中心的都市圈又具有建設千萬人口特大都會的動力。因此,在重慶市域內具有充分的余地和足夠的動力,來做這種以“地票”為載體的城鄉統籌。例如巫溪、奉節人均退耕還林20畝,可以折算為永川、萬州人均500平米建設用地指標、或是渝中、江北的人均300平米建設用地指標。
當前,黨中央國務院將重慶辟為城鄉統籌綜合試驗區,因此,“地票”的思路在重慶先行先試,“全國地票”不成熟,先做一個“地方地票”,有可能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
問題2:“地票”與移民城市福利的折算
從遷入地來看,生態移民進城所帶的“地票”一旦落地,就是對于當地城市發展建設的一項貢獻。“地票”所帶來的土地指標增加,應當與生態移民所應享受的城市居民福利全面接軌,這就涉及到生態移民戶籍向城市的遷徙,否則不能確保城市政府對于其各項保障和福利的支出責任。這樣,一張“地票”帶來的一份用地指標中,有多少折算成生態移民進城之后的保障和福利,多少折算成進城之后的基本住房保障,多少折算成移民的搬遷補助,多少折算為城市公共產品的增容費,都需要在遷入地的城區明確。這些都將直接影響到未來土地出讓金的使用。
從遷出地來看,生態移民的下山進城,往往是以梯度形式進行。即由高山下到中山,再由中山進入縣城,而縣城的人走進另外的城區。居住在山區的農民交出承包地,走向城區的人得到了城市的市民待遇,這在操作上又因公平問題會帶來新矛盾。重慶市政府應以怎樣的政策支持山區縣作為進一步鼓勵生態移民下山的杠桿,也需要量化。
問題3:“地票”交易如何在山區縣和城區之間完成?
從山區縣來說,退耕還林就應當核發“地票”。但是,“地票”是落實到人,還是落實到縣,涉及國土部門核發“地票”的具體手續,需要具體的研究設計。
生態移民進城,可能具體地體現為從高山下中山、從中山到平壩、從平壩的農村進入縣城、從山區縣進入城區的一系列傳遞過程,因此不僅在山區和城區之間,在山區縣的內部也要建立一系列的獎勵措施。
落實到人,核準的難度很大。可以將用地指標在重慶市域內各城區與各區縣間結算,例如在山區縣劃定退耕還林的范圍,以五年為期,在本縣內,人下山即給予獎勵,縣里墊付、期終結算。直到人口在山區和城區之間流動時產生“地票”,山區退耕銷戶的效應終于傳遞到城區進人擴容。
問題4:“地票”是否與計劃生育掛鉤?
“地票”的思路,最終是將人類活動從生態敏感地區的退出與城市化結合,體現的是人類對于自然環境壓力的減緩,因此,一定要與計劃生育嚴格掛鉤。但是從農村現實看,山區往往是計劃生育的薄弱地帶。超生戶得不到“地票”的激勵,會滯留在生態脆弱地帶,但是如果不與計劃生育掛鉤,相當于鼓勵超生。這會讓“地票”政策又會冒“種瓜得豆”的風險。
問題5:“地票”的流動要尊重農民的選擇
生態移民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決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簡單一刀切。只要不是像三峽水庫這樣的具有倒計時的項目,農民要不要下山,要不要進城,要進哪座城,最終都應由農民自主選擇。政府只需要把政策設計好,把賬給農民算清,最終的選擇權應當還給農民。
生態移民從山區進城,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不斷地比選、不斷地調整。“地票”一旦變現為各種城市的福利,是否會妨礙移民的再流動?我想,那時的流動已經大不同前,那時的流動是作為一個城區居民的流動,擁有城市的資產,市民的身份。無論心理結構、資產結構都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可以說,有沒有“地票”,生態移民都會再流動,但是有了“地票”,流動的過程就會更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