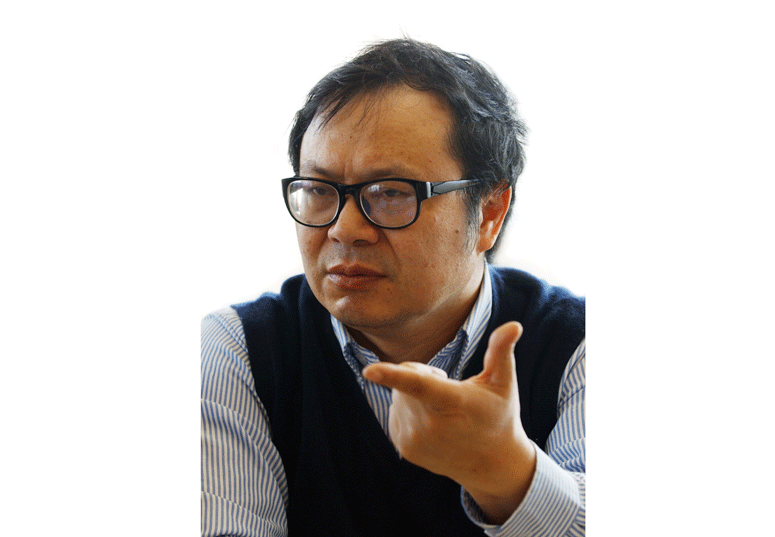城市觀
當(dāng)代藝術(shù)家
徐冰
+城市軌跡
2008年,定居紐約18年的徐冰做了一個(gè)重大決定:返回北京,擔(dān)任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副院長。他的折返讓不少人詫異,可對(duì)于他來說這是個(gè)必然“看夠了紐約,理解了西方的當(dāng)?shù)厮囆g(shù)生態(tài)就該回來了。”
徐冰在北京成長、學(xué)習(xí)、教書,也是在這里琢磨出了讓他蜚聲當(dāng)代藝術(shù)圈的《天書》。憑借《天書》的影響力,徐冰在上世紀(jì)90年代初去了西方當(dāng)代藝 術(shù)的中心之一紐約,“紐約讓我理解了西方當(dāng)代藝術(shù)的一種規(guī)則”。而2001年那場(chǎng)紐約劫難也賦予他靈感,用世貿(mào)大樓倒塌揚(yáng)起的灰塵所創(chuàng)作的《何處染塵埃》 巧妙地結(jié)合了災(zāi)難元素與中國的哲學(xué)名句,這件城市作品成為他另一個(gè)不得不提的代表作。紐約也因此成為和北京并列的徐冰最重要的人生坐標(biāo),正如他自己感嘆的 “紐約和北京是兩個(gè)讓我有理由生活下去的城市”。
他也許是中國知曉了最多秘密的人,因?yàn)樗麜鴮懥恕短鞎贰D切┧圃嘧R(shí)又陌生的中國字是徐冰獨(dú)自在北京的小屋中耕耘了2年的結(jié)果,而也正是那4000多個(gè)沒人認(rèn)識(shí)的中國字帶著他離開北京,定居紐約,再折返北京,這件舉世的作品亦成為他立足當(dāng)代藝術(shù)圈最有力的憑證。
曾離開北京多年的他,面對(duì)這個(gè)城市早不同于18年前的模樣,卻沒有如大量公共知識(shí)分子、藝術(shù)家們那樣的痛心疾首,“北京的變化很大,這些變化是 自然和必然的,說不上好或不好”。就像他自己也喜歡有歷史感的城市,卻強(qiáng)調(diào)沒有理由讓某些城市居民一直生活在所謂的沒有被現(xiàn)代化的城市和關(guān)系之中。
為500平米的土地設(shè)立咨詢委員會(huì)才是城市人性的開始
總有人惋惜著北京歷史感的逐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張揚(yáng)而現(xiàn)代的央視大樓、讓演員宋丹丹在圍脖上驚呼“放過北京”的SO H O建筑群,于是,我們會(huì)試想如果一個(gè)成功的當(dāng)?shù)厮囆g(shù)家成為了北京的管理者,那么北京的未來是否會(huì)有所不同?
徐冰的答案是改變需要從對(duì)每一塊土地的珍視開始。“目前我正在為紐約的下城,即布魯克林橋曼哈頓這一端,設(shè)計(jì)一個(gè)小小的公園及公共藝術(shù)品。”他 強(qiáng)調(diào)這個(gè)公園可能只有500平米,“其實(shí)是塊非常小的三角地,但是就為了這個(gè)項(xiàng)目,招標(biāo)了無數(shù)次,還需要找地方居民代表,其中包括老年組、華裔組及青年人 代表等等大家一起來參與討論這塊地的未來。”
他笑言過程非常復(fù)雜,“這些程序和謹(jǐn)慎態(tài)度無疑說明了城市對(duì)這塊土地的珍惜,而在中國,無論是多大的地未來要干什么,作出決策的也只是那么一兩 個(gè)人”。一個(gè)城市如果要做到人性化、合理化,無疑對(duì)土地的使用是需要謹(jǐn)慎且反復(fù)考慮的,“必須得專業(yè)化起來,但專業(yè)人士能夠發(fā)揮多大的作用在今天其實(shí)還是 個(gè)問號(hào)”。
徐冰直言這個(gè)時(shí)代一切都加速,連拆的速度也變快了,利益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環(huán),“領(lǐng)導(dǎo)們要搞形象過程,開發(fā)商們要顯示自己的財(cái)富和與眾不 同,而設(shè)計(jì)師為了獲得機(jī)會(huì)去拿到項(xiàng)目,則一定會(huì)去顯示自己的設(shè)計(jì)感,一定要讓甲方看見這筆設(shè)計(jì)費(fèi)的結(jié)果,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gè)悖論,因?yàn)檎嬲玫脑O(shè)計(jì)是看不出設(shè) 計(jì)痕跡的”。
“城市管理是個(gè)綜合事物,需要考慮整個(gè)城市的生態(tài)、功能設(shè)施、人群關(guān)系等等,所以藝術(shù)家是當(dāng)不了市長的。”徐冰笑言。對(duì)當(dāng)下中國來說,美感可能 在城市建設(shè)中還處于很次要的位置,“一切建設(shè)都由甲方?jīng)Q定,甲方的品位和希望,甲方的想象中有經(jīng)濟(jì)、資金的考量,有吸引用戶的考量”,也許缺的獨(dú)獨(dú)就是那 份美感。
徐冰雖然說,現(xiàn)在去改變北京太晚,卻依舊對(duì)這座城市心懷希望,“時(shí)間到了自然就會(huì)解決,因?yàn)橥ㄟ^提高人的素質(zhì),大家會(huì)認(rèn)識(shí)到美感與歷史的重要,比如現(xiàn)在對(duì)北京城墻的反思”。如果從現(xiàn)在起,北京500平米土地的使用都會(huì)由咨詢委員會(huì)來探討決定,那么遺憾會(huì)不會(huì)少一些?
城市里長滿過度設(shè)計(jì)的建筑,映射追求名牌的心態(tài)
徐冰曾在布魯塞爾的中歐文化論壇上,與那座用力過猛的央視大樓設(shè)計(jì)者庫哈斯探討過相關(guān)意見,“我認(rèn)為庫哈斯沒有明白他的問題在于他對(duì)自然環(huán)境的 不尊敬,不管他的大樓是如何的當(dāng)代,結(jié)構(gòu)是如何有新意和有貢獻(xiàn),但這個(gè)建筑對(duì)周邊的社會(huì)、人文、自然環(huán)境缺少尊重的態(tài)度。中國人審美觀的本質(zhì),對(duì)自然是尊 重的,很多優(yōu)秀的建筑都是如此,有著依勢(shì)而生的天然”。
也許在很長一段時(shí)間里,中國都不能擁有一個(gè)藝術(shù)家市長,但藝術(shù)家或許能夠用曲線的方式“挽救”北京,就像徐冰自述他的藝術(shù)態(tài)度就是生活在哪里就 面對(duì)哪里的問題,“你所生活的城市,你直接面對(duì)的問題,它隨時(shí)隨地都有可能激發(fā)你的靈感”。于是他創(chuàng)造了《鳳凰》帶領(lǐng)人去思考城市化背后的意義與得失。
徐冰也在思考過度設(shè)計(jì)與當(dāng)代社會(huì)符號(hào)化的關(guān)系,“符號(hào)化是我們文化中重要的內(nèi)容。在古代、在有大量時(shí)間的時(shí)代,符號(hào)化可以讓人的想象力發(fā)揮得非 常充分,可以讓形而上的部分得到充分發(fā)展,我們能從古代藝術(shù)的意境和古詩詞的高度中領(lǐng)會(huì)到這一點(diǎn)。但在當(dāng)代,在沒有耐心和深度的時(shí)代,符號(hào)化會(huì)造成人類、 城市低智化的傾向。你看,為什么中國有這么多奇奇怪怪的大樓,這么多過度設(shè)計(jì)的東西?都是基于對(duì)符號(hào)化崇拜,追求名牌心態(tài)的結(jié)果”。
“名牌傾向”這個(gè)問題中國人乃至亞洲人最嚴(yán)重,為什么呢?徐冰解釋,因?yàn)闈h語文化圈的人對(duì)符號(hào)特別看重并帶有敬拜情節(jié)。名牌其實(shí)是一種符號(hào)化的趨向,穿的是一種符號(hào),而不是衣服本身。中國建筑項(xiàng)目喜歡大牌建筑師,看重的是符號(hào)而不是建筑本身。
你不能因?yàn)橄矚g古舊的城市而反對(duì)居民享受當(dāng)代化
懷念過去漸漸成為風(fēng)尚,可徐冰對(duì)此有自己理解的角度,“這件事情底層與貴族、知識(shí)分子的需求截然不同。其實(shí)我不喜歡一些人對(duì)某些東西改變或遺失 只抱遺憾的單一態(tài)度,比如到了一個(gè)小城市看見牛車、水車,人們還挑著擔(dān)子,就覺得太好了,如果這些事物消失變成樓房他們就覺得無趣,但生活在這里的人要享 受當(dāng)代化的生活,誰都沒有權(quán)力讓別人停留在他的視覺愉悅的階段上”。
雖然徐冰也偏愛一些歷史、政治和社會(huì)痕跡重的城市,如北京、紐約、柏林,“北京最大的魅力就是豐富,故宮的護(hù)城河和宮墻間的那段小路是世間絕美 的景色”,也對(duì)一些無聊的城市無感覺,“受不了美國中部的一些小城市,也許非常干凈,但很無趣沒意思,那些地方太標(biāo)準(zhǔn)化,你坐飛機(jī)去任何一個(gè)地方都像沒換 地方一樣,我不能生活在這樣的城市”,可他說這只是個(gè)人觀感。“的確有些城市你覺得無聊、不好看,但你沒有理由不讓它這樣,你沒有理由讓一個(gè)城市的居民一 直生活在你喜歡的沒有被全球化的關(guān)系之中。”
徐冰說目前的世界是由資本利益所左右的世界,幾乎任何城市都有著相同的國際品牌與符號(hào),“不能因?yàn)槟阆訔壊缓每淳筒环胚@個(gè)符號(hào),問題是當(dāng)?shù)鼐用褚畹脤?shí)惠化,也許它不好看但它便宜它方便,這時(shí)候美感一定是放在次要的位置”。
■ 深圳觀
深圳從土氣的城市變得和其他城市沒什么區(qū)別
徐冰最近一次造訪深圳應(yīng)該是2009年來何香凝美術(shù)館做“木林森”項(xiàng)目,他和一群深圳孩子還有家長們完成項(xiàng)目,“那些孩子和家長對(duì)待藝術(shù)、對(duì)待 教育的參與熱情很高”。可他也遺憾地說同樣是“木林森”項(xiàng)目,還是肯尼亞孩子的畫給他最深印象,“我們的孩子畫的畫總帶著‘福娃’的影子,也是城市化了 的”。
肯尼亞孩子的畫在他看來更本真,“在藝術(shù)的世界里,本真的東西自然更受青睞,但我同樣也不能要求肯尼亞孩子永遠(yuǎn)生活在那樣的本真里”。
他對(duì)深圳還有個(gè)特別印象,“記得1993年我到美國后第一次回國,從深圳入關(guān)。那個(gè)時(shí)候深圳被炒得很熱,有內(nèi)地沒有的現(xiàn)代文化,來到以后呢,天 啊,深圳怎么這么土”?徐冰一直記憶猶新,“和我期待的太不同了,可能是香港太發(fā)達(dá),深圳還是個(gè)沒成型的城市”,而那些傳說中的海外文化也只是來自香港的 外貿(mào)服裝。
多年后再踏足深圳,徐冰覺得土氣沒有了但同時(shí)深圳變得和其他的城市沒有區(qū)別,“也再?zèng)]讓我留下和其他城市特別不同的印象”。